《风起陕甘宁》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以历史散文形式,聚焦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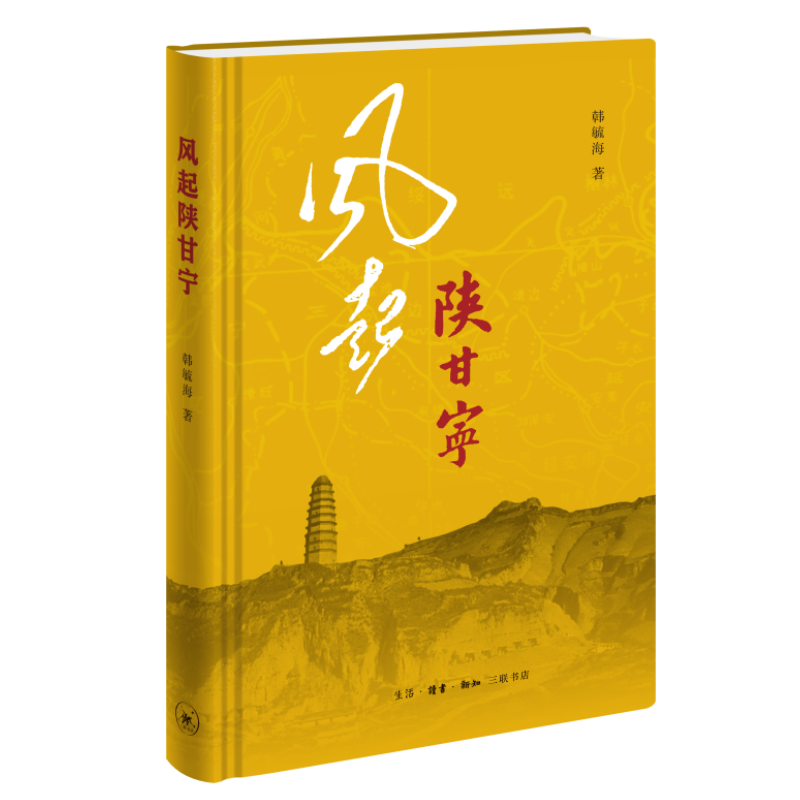
《风起陕甘宁》书本封面图。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风起陕甘宁》一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在2020年到陕北探访后,历经4年时间完成的通俗理论著作。该书由《杨家沟》《大地上的学问》《波罗》《王学文》与《结合》五个篇章构成,行文旁征博引、酣畅淋漓。从地域文化、地方性格的角度解读中国革命,以“陕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这一话题为出发点,充分利用丰富史料,结合实地考察,以生动描述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命题展开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林凤清)
《风起陕甘宁》
序
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韩老师,由共同的历史兴趣爱好与读书人的清议宏论谈开去,越谈越深,谈得兴起,问及他拟出版的或拟再版的作品,他拿出了《风起陕甘宁》。
《风起陕甘宁》,聚焦的内容是作者2020年秋天在榆林回望中国革命。书名进而内容,抓住了我,震撼了我。时间:2020年秋天,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个收获的金色时节。地点:榆林,黄土高原,年降水量400毫米,历史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交汇点,文化碰撞,雄浑厚重。话题:以一场时空之旅,在“延安十三年”的背景下,看黄土文明遗风与中国革命作风的激荡与结合。主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气质、意志品格的由来与走向,不论走多远,它都在我们的心底奔涌、在我们的上空闪烁,让我们成为大写的人、全面的人、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本书读来有三点感受最为强烈,就是“散与聚、杂与专、情与理”交织贯通,充满着辩证统一。从容自如,大气而不拘泥,灵动而透着深刻,是本书精神实质与表达风格的主基调。
一是散与聚。
看似散漫、实则神聚。沿着“陕北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这一话题,跨越中外,纵横古今,上天入地,但都紧紧聚焦于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与战略、思维。
书中,韩老师引用钱穆先生的观点:一个民族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黄河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的特点,就是激流勇进、在激流中拼搏前进。
韩老师带着自己的思索与探究,走访了榆林市的横山、吴堡、米脂、绥德这些充满传说的地方,接触了鼻音浓重、庄重幽默、保守浪漫的陕北人。
陕北人有其独特的性格,那是兼具草原的奔放与中原的保守为一体的性格,是兼具高原的自由与黄土的局促为一体的性格。陕北的革命者,是有着这样一种特殊性格的革命者,他们不乏理想但更为实际,热爱斗争却又重视人情,坚强但又宽厚,思想很现代但却看起来土里土气、土头土脑,充满了辩证法。辩证法,这是中华文明最好的东西,也是在中国西部保存最顽强的东西。
作者继续生发开去。谈及“一代学术奇人”陈寅恪曾从历史与战略的角度,重新发现了陕甘宁这个地方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联系。陈先生坚信“读史早知今日事”,“用学问讲政治”。他主张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西晋灭亡的“天下大乱”中,走出当时历史大变局的,正是陕甘宁地区胡汉贵族融合形成的充满血性的新领导阶级、胡汉文化融合形成的开放进取的新贵族文化、胡汉制度融合吸纳形成的新的“关陇制度”。
作者继续挥洒笔墨,得心应手地展开去。书中提出党内有两个天才智囊,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博士冀朝鼎,一个是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博士王学文,如果讲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就不能离开这两个人。
1937年王学文到延安,曾担任过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年之后,这所学校的日本学生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深情地回忆起王学文:有课的日子,他总是光脚穿着草鞋,头戴草帽,沿着宝塔山的山路上来。1979年7月访华期间,他们再次见到了84岁高龄的王学文老师,随后他们将一直珍藏着的当时记录的 授课笔记寄给了王老师,此件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重读王学文的旧作,不由让人们生出很多感慨。
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人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外在的市场—供给—需求—预期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人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的劳动、生产与实践决定的。前者讲外在的环境塑造了人的价值,后者讲人作为劳动与实践的主体,塑造了世界与人本身。只有抓住这一精髓,方才可以懂得毛泽东所 概括的经济工作的“四面八方”。“四面”其实就是指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四个方面,“八方”则是与上述四个方面相联系着的各个社会主体、社会各阶层,指工人、农民、工商业者、投资者等。根据这一精彩的“四面八方”说,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唯生产力论不对,是一种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讲成阶级斗争、打倒一切更不对,是教条化。毛泽东所概括的“四面八方”,可谓神来之笔,这才是用最精彩的中国语言,讲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作者感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理由当然有很多,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文化优秀成分结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手下有许许多多王学文这样的能人、赤脚的教授,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自己的学问与黄土地连接到一起。
至此,本书的主题主线又聚拢回来。
二是杂与专。
阅读本书,作者与作品、结构与文体似乎都难以分类。文学?但通篇以史而述。史学?文字表达渲染而飞扬。政治经济学?却又以文史来论“不平衡发展”、以历史地理来讲政治经济。党史研究专著?但也可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来读,集艺术性的“红色叙事”和个性化的 “重大主题表达”于一身。于是,看似杂家、实则专家,以多方面的专业知识、独立思考、个性表达融汇成一个 新的“专”,自成一家之说,而这也成为本书独特魅力之 所在。我所担心的,只是韩老师这套观点与话术不太好传承而已。
比如,书中的“陕北风俗”一节,起首一句竟是灵魂之问:“什么是政治与治理的最高境界?”于是,由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城邦的优良生活”“良风美俗”谈起,直到有着“乡绅乡贤”的互助合作的中国传统乡村生活; 由中国的“良风美俗”植根于乡村共同体谈起,论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结合。读到这里时,竟也激发我突然“杂乱无章”地想起一个有点“高精尖”的专业问题:如果我们有效地控制了资本的野蛮生长,形成了良性有序的网络空间,网络平台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力”和小微企业、创意人才、快递小哥代表的“小生产活力”结合起来,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比如,第一篇从毛泽东曾住过四个多月的杨家沟讲起,但作者观察和入笔的维度与众不同,从而触发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杨家沟其实是个屹立百年的小城堡,名叫扶风寨。扶风寨是典型的“坞堡”建筑。所谓村,起初就是寨,也是魏晋时代的“坞堡”,当时人民自相纠合,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坞堡”与基层的邻、里、党制度,成为中国“大一统”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组织形式一直最顽强地保留在西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武装割据的历史就此开始。作者给出点睛之笔:“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比如,在第二篇中讲到冀朝鼎。这个父亲曾任山西司法厅厅长和教育厅厅长的名门之后、“自我扬弃的主人”,这个年仅13岁便考入清华学校、五四运动中被抓的最小的学生,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美国政界与学 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这篇文章把马克思论述过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问题讲得很透彻,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认为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 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基本经济区建设,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建设达成的;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导出的结论,就是只有通过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战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于是,作者自问自答,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出路在哪里?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有了这样的视野,就可以再来看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 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实现了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接合带”的革命化。从一定角度看,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以草原山地文明包围基本经济区、占领基本经济区,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治理体系的过程,是内涵一致、有机契合的。中华文明在 这两大区域的融合中,不断走向复兴。“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那是把我们带进空间与时间、宇宙与历史之中的何等的想象力。而作者也常常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具体的场景下,把我们引向宏阔的历史,延伸出某种无限的遐思。
比如,第二篇“大地上的学问”,从各种关于共同体的论述展开去。作者指出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支配人类社会。接下来,作者又是一个神来之笔,以他特有的跨 越时空的思维与逻辑,再次宕出“神来之笔”:“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的手里,于是,最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从水利与定居,战争与贸易,劳动、技术与资本几个方面,深刻描述了人类共同体的不同形式,而我们要真正地理解这些艰深的理论,只有去深刻 地理解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什么是中国道路?作者以第五篇的标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道路,就是“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
做学问可以旁征博引,也可以庞杂琐细,有思考有见地或能够给人启发就好;但务必要专,要深入扎根在 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上。
三是情与理。
作品饱含着炽烈的情,阐述了革命的理,带着我们 从原理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革命,去重估“为了真理而斗争”这句话的起源,去讴歌自由与人性:“自由还意味着:人是为了真理、为了信念,可以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存在。”
陕北的性格,既融入了此前中国革命的风格,也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性格,使得革命者的性格中,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具有了黄土地的宽厚与博大,既有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意志,又有了同志式的温暖和浓烈的人间情怀。正如横山信天游里唱的,“三号号的盒子红绳绳,跟上我的哥哥闹革命。你当红军我宣传,咱们一搭里闹革命多喜欢”,多么浪漫,何等多情,既慷慨激昂又婉转曲折。作者就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具体描述,通过一些极富画面感的场景,牵着我们感同身受地重返历史现场,塑造出真实立体、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党的形象。
书中第三篇是由榆林的“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讲起,展开对古今中外志士仁人放下自我、献身革命、救苦救难的思考。“什么叫做人的境界,什么叫为人的觉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什么才是‘书生意气’?这些确实是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从来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于是,他从打破“从来都是鞋匠造反,要做老爷;当今却是老爷们造反,为的是要做鞋匠”这一传统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讲到了1946年10月解放战争初 起胜负未定之时陕西望族胡景铎、胡希仲叔侄毅然在榆林横山波罗堡通电起义的壮举。
习仲勋与胡家叔侄同窗共读结下一生的情谊,正是在习仲勋的“接引”下,胡家叔侄走上了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道路。正是陕北这块热土上的“乡党气节”、家国情怀的“情”,与科学真理、革命学说的“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一朝觉悟,胡家叔侄如此,中国革命也在陕北寻求到了走上光明、美好世界的“大智慧”。
作者一直在探究,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当然,这是因为有理想信念、有铁的纪律性。一个坚强的党,一个坚强的领袖,一个坚强的组织原则,这就是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是第一法宝。但只有这个还不够,我们党还有第二个法宝,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 泽东思想的精髓,能讲辩证法、“会拐弯”。毛泽东在杨家沟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
历史的理与人间的情总会交织的。
读罢,想起韩老师的另一部成名之作《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他拍案激赏马克思不仅是思想革命的大师,也是文体革命的大师,盛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创了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熔为一炉的综合视野,盛赞把思想与激情、知识与才华、庄严与诙谐、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熔为一炉的叙述方式,感叹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思想,有思想的人不一定有才华,而把知识、思想、才华如此高度地凝练起来,这就是马克思的风格。我私下忖度,韩老师从内心深处是把马克思作为导师,是一个“马粉”,可能马老师的表 述风格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韩老师。
在紧张的工作与学习之余,翻翻这本书,看看这本 内容丰富、境界宽阔的“主题读物”,回顾下历史、重燃下激情,引发我们的一咏三叹,定当有些教益。
读了《风起陕甘宁》,感触颇多,很发了些议论,我和韩老师的一位朋友就鼓动我把它写出来。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蒙韩老师不弃,是为序。
黄志坚
2023年6月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