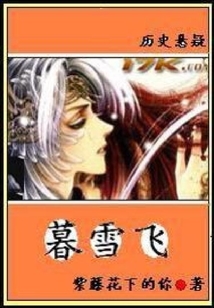
暮雪飞
最新章节
书友吧第1章 引 子
二十年前,我在河南安阳的一个乡下,听到附近一座老宅时常闹鬼的事。说来奇怪,大凡有了鬼魂故事的房子,是住不得人的,然而乡民告诉我,屋子里偏偏住着一个老太婆,数十年如一日,白天很少出门,没人说起老人的身世,不记得她的真实年龄,兴许因为担心或者害怕,路上碰见,人们便远远避开,生怕沾了她身上的一丝灰尘,也会把鬼魂引到自己家里。当我把打算探访的消息告诉他时,眼前这个老实巴交的乡民嗫嚅了半天才说:“那老人你是见不得的。”没有理由,像是恳求,更像是责怪自己多嘴。我说:“我看房子,不看人。”算是给了他一个交待。
我沿着黄尘飞扬的大路走了十余里,最后拐上一个名叫“三大夫”的土坡,三大夫是三棵古松的别名,当时已是黄昏了,老宅不出所料地构筑在一片黑松林里,林子外的小河干涸见底,我还是选择从木板桥上过,吱吱嘎嘎的声音像是对屋子里的老人打着招呼。
我为自己顺利抵达舒了一口气。老宅沉浸在暮霭中,大门前的几丛枯草结束了一天的摇摆,想到客人不会将它打扰,反而又闪了一下身。它们能见证我的到来,便与此刻的时间无关,而且,这一声昏鸦似的老宅也已将时间的沧桑演绎得足够从容。我有意在大门外转来又转去,这一刻停留,能让我的思绪适应周围的空旷。
我沿着墙根走了一圈,夜色笼罩在我的四周,大墙马头露出它诱人的安静的魔力。我发现,老宅外墙的每一个细节象刀锋一样都无可挑剔,像是发觉墙外有人,厢房里亮起了烛光,烛光象窗户纸一样笼在窗口,目光倘佯在烛光与大墙马头之间,就象逗留在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语中间,他们被时间搓揉的如此完美,以至于浑然一体。
许是不忍心将我长久地拒之门外,老妪开一扇小门将客人让入院子里。然后象一个幽灵沿着廊庑,依次打开了十来盏廊灯,晕黄的灯光,象一个个逗号在一番沉思中现显出停顿的意义,我几乎是毫不费力就捕捉住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普鲁斯特认为艺术力量高于个人的悲悯,恰恰相反,现实大于语言。墙头外黑夜如雪便是有力地见证。站在院子中间,连厢房二十来间房子仿佛一副不经意的素描,在我感到冷落时,却有某种力量在悄然涌动着它的背脊,不能不让我联想到这样的诗句:
“你看不到,但感觉得到。”
走廊上粗大的柱子,象一排凝固成条形的时间,支撑起黑夜的穹窿。触摸柱子上插得进小指的裂痕,退潮后留下的缺憾,不正是岁月的沟壑吗?老妪道:“客人还是先到堂上去看看吧。”换一个地方换一番感触,但持久是这里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头带给我的深刻印象。在诗歌中,捕捉一种感觉是多么艰难,而在这院子里,我听到马车在官道上驱驰,烟尘纷乱,河流两岸的山坡静静矗立,月光布满天空。这东西厢房紧闭的房门突然打开,我才不管我是否就是一堆夜色是穿堂的风,有了这个老人,老宅便变得充满起来,那被开门声打断的时间就象括号里的空白,让你无所顾忌地施展你的想象。
我也丝毫感受不到鬼魂的压力,甚至怀疑乡民的所有解释无非是一份私心。主人留下的印迹无所不在。高耸的挡墙遮住了远山那一抹清新,亦足见起屋的主人不是一个天性浪漫的人,门额“虚怀一是”四字足以说明他守成的学养。临廊板壁上一点不经意的装饰,让人们得以窥见主人的胸怀,宛如一个虚词挽救了整首诗歌,覆盖着它终将水落石出的完美内涵。石级到处可见,然眼前的石阶让我对大堂产生一种仰视的感觉,这就是沉湎于心世代延续的必然的敬畏。敬畏的美,是需要彼此之间的距离,在某个中午的空白处敞亮地渗透。
踏入大堂,匾额“岁荣堂”三字褪去了朱颜,但书写者沉雄的腕力仍然从刀痕中显露无遗,在老宅立基之时,总能找到写得一笔好字的人,当我们觉得“偶尔”是那么令人神往,在当时不过是一杯经过侍女的手传递的茶水;“徐丰生”的落款虽然陌生,但能将自己的思想在空宽处延伸数百年,总是一种幸运吧,在我到来前,它一直这样寂然无声的张挂着,没有要求体验的注视,没有苟且生活的叹息,但它依然在一个例外中存在,仿佛时间也沾染了晋人风骨,谁说这老宅历经百年风雨而不凋敝,不正是这一笔好字镇压的缘故吗。无名是最深的寂寞,当人世间缺乏了那种莫名的感动,在老宅深处,你块然行走在蔓草岁月间,这种感动却是不期而遇的。木鱼梁上波浪滚滚,坐在烛影摇曳的角落里,也能听到这一册古籍夹缝里大海的心声。
老宅的一砖一瓦如文字的片段,被岁月串连成篇,东墙上的这个花岗岩族徽,恰是文章的中心,成了我们驻足的理由。那是一朵盛开的菊花,难得有那么灿烂如微笑的菊花,选择菊作族徽,其意义不言自明,虽然我未必要看到菊花才想到这座宅子的主人,在我还在门外逗留时,眼前早出现了一张宽厚的脸,线条简洁,轮廓模糊,一部《论语》端出一部完整的人生;但我想,以主人那种老于世故的严实家风,这菊花更多的是体现它的深远。郁达夫望见杭州的城堞联想到丛残的往事,慨然长叹人生的无奈与寡助,我却很是羡慕屋子主人那番闲适,这在今天是很难得的作为了,而在当时学究也罢,世故也罢,骨子里都有这份闲适在,以至于出现了宽敞的大堂,花园式的明堂,梁柱牛腿上那栩栩如生的花雕人物,没有一双足够欣赏的眼睛,谁来叹羡它的虚华呢?
“这里曾发生过什么吧。”我问老妪。
“客人是百年里来到这儿的第一个访客,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老太婆也经不起年轻人的挑剔打量了,但能跟我说话,老太婆已经很满足了。既然你打扰了我的宁静,你就再也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唠叨,我都闻到泥土的气味了,再不把藏在每一块砖缝里的往事抠出来说说,或者象外头人说的晒晒太阳,世人就真的不知道这屋子的前生后世了。”
这正是我期待的。
“客人听说过‘回雪刀’吗?”
“回雪刀?”我一时没缓过神来。
史载“宋时匠人韩氏,误入前朝太庙,得一废刀,血色,乃居深山七年,重铸,雪日始成,铭曰回雪,性寒,凡人莫近。后归宋相秦氏。”明人高启在《摭异记》里,认定宋人韩氏所铸宝刀的前身,便是升明元年地下掘起的上血刀。此刀每换一个主人,“有献必鸣”,秦桧死后,宝刀不知下落。
“客人是听说过这件宝物的。”老人见我迟疑,竟然象遇见了熟人一样露出了笑。我终于是正面瞧着她了,她的牙齿几乎掉光了,不见牙齿遮拦的笑,才是最让人放心的真实的笑。
“回雪刀可谓史上最神秘的一口宝刀。据高启记载,自元仁宗延佑三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间,死于寻刀人之间仇杀的不下千人。杀戮之重,莫过此刀。老人家说的就是这一口宝刀吧。听说宝刀周围的护刀人个个身怀绝技。传言说,回雪刀不见是福。其实是寻常人无法近身的说法。”
“你知道得还挺多的。听说过护刀人的事吧。”
“往事久远,便是皇家典藏也已散落殆尽,何况只是传说中的一口宝刀呢。历史上纵然真的出现过所谓的护刀人,如今冷落星散,已经无迹可寻。”
“老太婆就是最后一个护刀人。”
“你?”
我真的很惊讶。世上关于护刀人的传说很多,轰轰烈烈,极富智慧,但最后竟落在眼前这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女人身上,落差之大,让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跟一个鬼魂在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不奇怪。你眼前这座院子是它最后的归宿。刀在你的心中,你也是护刀人。”
“能否让我一睹真颜?”我简直迫不及待。
“你是嫌老太婆说话啰嗦。客人已经看到了,只是我不说,你不知道。”
我只看见屋子,以及屋子里的陈设。我竟然记不得自己哪里看到过此刀,甚至形状象刀的东西。老人跟我讲了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后,见我仍然浑浑噩噩,不得要领,终于是失望了。
“那客人请走吧。”
我是该走了,不求甚解方能来去从容,无弦琴的曲子如杯子里的波纹弥漫在闲言赘语中,宝刀自有它的情缘;那离奇的陈年旧迹在黑色的覆盖下,已不忍人们来惊叨;我只是纳闷,那渴望自由而将灵魂托付于大堂巨梁上的女主人,她注视的山峦在当时真的是“山乱知雨在,一望沧海远”吗?她脆弱的心灵又何以不能承受那年轻人“英俊出吴越,秋水澄江湘”的感触呢?戛然而止总是比余音袅袅来的隽永。“岁荣”两字,往远处看,给人以进取,但终究摆脱不了宿命的泥潭。
我其实是在寻找着一篇传记,扑面而来的却是凌乱不堪的历史故实,所谓的秩序只是史家的一厢情愿。回雪刀的历史是屋子主人无法梳理的,缺乏文字记载恰恰是它的幸运,在车水马龙不知月光为何物的今天,被人误读远不如被人遗忘值得庆幸。人生的终点大多是默无声息的,就像林子里吐出的风一样。当我转身离去,那居停老妪“嘭”地关上小门时,唯有几丝枯草注视着我的背影。但对一个“惊起却回首,有恨无人省”的夜行人来说,这已经足够。而我也惊奇自己始终没有慌乱,那关门声令我满载而归。“嘭”的一声,语言就这样展现出它全部的秘密。
但促成我把回雪刀的秘密写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在去年十二月,我因此凭借记忆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一座老宅,终于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一切,尽管只是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内心的感动依然那么强烈,就像是发生在昨天身边的事。
时间回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秋。
朱元璋时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甲士二十五万,直取山东诸郡;命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率湖广诸军攻取广西,战场在东西两端呈扇形摆开,反倒是中原百战之地,兵祸未起,独得一爿安宁。通往洛阳的几条道上,车来人往,黄尘滚滚,一派繁忙,丝毫不见战争来临的迹象。
中午时候的太阳还是颇毒,赶车的,骑马的,挤在路旁的凉棚里,喝茶稍歇,其中,江南风威镖局的人占据了北边一大块地方,赶在黄昏前进城,时间还颇为充裕。午歇未足,只听得对面岔道上马蹄声急,三骑马无所顾忌直冲过来,一阵黄土跟着卷进凉棚,众人手上的茶碗里立时泛起一层灰尘,苑镖头是松毛性子,一点就着,旁边李镖头便去捂他的嘴,那骂声还是从手指缝里漏了出去:“想找个地方撒野不是------”
一条软鞭便从人堆里窜了进来,长了眼一样地找上苑镖头的脖子,苑镖头只觉得喉头一紧,身子便软了;那鞭子随即又缩了回去。苑镖头还没明白过来,只见三骑马像屏风一样挡在棚子外面,马上二男一女头戴斗笠,正向棚子里四处察看。两个男的三十不到,一身书生穿着,嘴角含笑,神情轻佻;斗笠遮住了女的一半的面容,苑镖头只瞧见她小巧的鼻子,但已觉得这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半张脸,自己刚才的确是冒犯了。
那女的微微抬头,正好与苑镖头四眼相遇,苑镖头直直地盯着她看,那女的突然露出清甜的笑:“刚才我没为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声音软如溪水。
苑镖头摇摇头,半天才斗胆道:“姑娘的心思,小生不敢琢磨。”
那女的道:“这就对了,说话不能由着性子来。你模样俊俏,眼睛里风生水起,是前世修来的福,被鞭子慢慢勒死,会让人折寿的。这样吧,你自己随便在脸蛋上划两下,咱们的结就算是解了。”
她身边的两个男人便笑了,其中一人眼睛细小,让人觉得总是在打量着你,另一人年纪稍长,左颊长着一颗淡淡的痣,道:“这人机灵,妹妹本可以好好消遣一番。只是武功不行,要尽兴就做不到了。三个月后,我们做哥哥的再给妹妹物色一个称心的,算是今天匆忙之间的补偿吧。”
领头的曹镖头胖墩墩的,一副富商模样,就在三人刚出现时,已悄然解下背上包裹。听到“三个月后”一句,将包裹交给孟镖头,慢慢地走到众人前面,满脸是笑:“这不是冀中三侠吗?这位是烟絮无痕何碧何女侠了。在下姓曹,和几位兄弟路过此地,不期能一睹三位大侠真颜,真是三生有幸,便请进来喝口凉茶躲躲日头,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走。”
刚才说话的大哥道:“你心里只怕在说自己前世不修。言不由衷,但听着舒心。我也不为难于你,你自己拿来吧。”说着在曹镖头面前摊开一只手掌。
苑镖头想不到一句话撞上了这三个魔头,脸色已灰败,他身边一人如梦呓般吐了一句:“年轻人哪就爱多嘴多舌。”低头一看,却是早先坐在凉棚里的一个灰衣老头,老头喝够自己带来的酒,正枕着手臂小睡。苑镖头闻到酒香,更被他这句话一撞,胸中生出一股豪气,右手便去寻找腰刀。
曹镖头稍稍一愣:“弟兄们得罪之处,捎个口信,立马赶往府上赔不是。何必劳驾诸位大老远地赶过来呢。我这里备着一百片金片子,先请笑纳,日后另有补报。”从胸口掏出一只绣着肚兜小儿的荷包。
那人“哼”了一声,一把接过:“你装糊涂,大爷就笑纳了啊。小妹,你也不必客气。”
听得那女的答应一声:“好。”鞭子应声扬起,苑镖头便觉得眼前一黑,大叫一声,一阵撕裂的痛直贯全身,他一抹脸,明知是血,却什么都看不见。众人见他眼窝里鲜血冒出,顿时乱了。那鞭子呼啸着反卷过来,孟镖头眼疾身敏,侧身让过,鞭子卷走了他手上包裹。
正是曹镖头刚才解下的包裹。曹、孟两镖头大呼着抢身而出,但只跨出棚子一步,便双双倒地,两人翻身而起,三骑马行雷一般早已远去。
曹镖头拦住众人,转身喊道:“孟镖头留下,替苑兄弟包扎好伤口再走,其他人赶快上马,跟我走。”
刚说完,那阵令人窒息的马蹄声又在耳边鼓捣起来。那三人驰卷而至,正好把众人堵在棚子边上。
苑镖头大叫道:“贼女人,老子跟你拼了。”他双眼已瞎,在乱哄哄的凉棚底下,竟是寸步难行。曹、孟等人看到三人去而复回,已知就里,纷纷拨出钢刀。
三人却没有了刚才的匆忙之色,脸上挂着笑,任马匹来回倒动。那大哥声音亲和:“温某自出道以来,还从未失手过,今天差点栽在你等手里,心里惭愧的很。所以又回转来看望大家。”
此话让曹、孟等人不知该如何回答。苑镖头尖利的叫声又起:“曹兄,‘冀中三煞’心狠手辣,何时跟人攀过交情,大伙儿就等你招呼了——”“了”字在众人耳里滚动如雷,但谁都没动。
那女的道:“你倒是条汉子。”
“闭嘴。”苑镖头情急之下,“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这口血提醒了曹镖头,偏偏曹镖头不是能拿主意的主,回头瞧着孟镖头。这一迟疑,那女子手里的软鞭象手指一样灵活地跃入棚子里,却出人意料地直奔众人身后的一个少年,少年中等身材,看他穿着打扮,也是镖局中人,同样背着一个青蓝色包裹。这少年眼见软鞭窜得身前,伸手便抓住了鞭梢。
女子一惊,用力一拉,鞭子竟然扯不回来,随即松手,软鞭倒卷出去,身子如一片落叶被风从马背上吹起,手里早多了一柄弯刀,空中拖过一记旋弧,刀锋直逼少年抓住软鞭的左臂。手法曼妙,刀锋如轻纱飞舞,众人都看的呆了。
忽见得寒光一闪,“叮”的一声,那飞舞的轻纱化作一缕薄烟溜出了棚子,软鞭断成数截散落地上。看那女子,斗笠随风飘落,一头青丝如瀑布直挂下来,脸上肌肤吹弹得破,美貌得让人不敢多瞧一眼。少年跟着一刀横削而至。这两下兔起鹘落,众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形势已发生逆变,却见那女子一动不动,眼睛眨了两下,突然露出花瓣似的微笑。
她两个同伴同时惊叫道:“小心。”少年出招奇快,两人不及施救,那刀掠至女子胸前便凝而不发。便在此时,只见女子伸出纤纤素手,滑过少年的脸,轻声道:“好刀法,姐姐记住你了。”
说罢,飘身上马,也不看同伴一眼,打马原路回去。苑镖头疑道:“怎么,谁走了?邓镖头,不能便宜了他们。”
少年对马上两人道:“还不快走。”
两人对视一笑,转过马头,事情似乎到此为止,却几乎同时从马背上跃起,空中如玉蟒翻身,双刀分削少年左右双肩。那少年长刀一抹,将身子封得严严实实,但‘冀中三煞’在江湖上的名头何等响亮,刀法自有独到之处,两人脚一着地,又是双刀齐出,只见少年前后两道电光疾闪过去,这便是刀法中的“踏雪无痕”,凭的是刀气杀人,不流一滴血便死了。
少年持刀而立,竟毫发无伤。
姓温的两人落在一丈开外,竟没看清少年如何出招,肩头已被对方手上的钢刀结结实实拍了一下,两人一脸沮丧,但随即宁定。“大哥,此人一刀便破了咱们的落叶刀法,说不定就是师父要等的人。”说话的是二弟。
那大哥道:“我刚才也那么想,现在没有了。他不可能是。”
二弟道:“咱们老是担心必有一败,却没想到败在一个少年手里。以后的日子因为少了这番顾虑,会过得很舒畅。”
大哥道:“三妹看不透这一层,回去好好劝说。”
二弟道:“小弟明白。只是咱们又让师父空等了一年。”
两人名声在外,愣着不走,众人不免慌乱,既听不懂两人说什么,也摸不到对方的心思,只盼着人家快走。曹镖头拱手道:“三位武功高强,让我兄弟们大开眼界,过去有误会的地方,我等给三位赔个罪,咱们不打不相识,这事就算过去了。”
那大哥笑道:“刚才跌了个狗啃屎,说话倒还伶俐。”说着两人便上马走了。
曹镖头再不敢停留,与那少年嘀咕了一句,走到苑镖头面前道:“兄弟,你糊涂了,不是做哥哥的不替你报仇,实在是吃咱们这碗饭的,关键是要夹起尾巴好生走路。”见苑镖头闭上眼,便招呼大伙儿快走。
凉棚里只剩下一个老头,老头已睡熟了。
是为引子。

